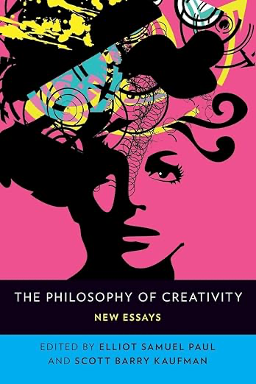AI加剧了“创造力焦虑”? 这里有一剂哲学药方
近年来,我们已看到了太多人工智能在文艺、科学等领域创造的奇迹,甚至对此产生了些许审美疲劳。比如,在美术领域,AI绘图软件MidJourney参与创作的绘画《空间歌剧院》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数字艺术竞赛获一等奖。主办方在得知作品的创作方式后仍决定向它颁发荣誉;在科学领域,人工智能模型Alphafold可以仅依据氨基酸序列,成功预测蛋白质的折叠结构。该成果被视为在蛋白质折叠问题上的重大突破。
然而,这些AI奇迹在很多时候带给人们的不只有欣喜,还有一种对人类失去创造力的焦虑。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人们应当珍视并培养其创造力——因为创造力具有巨大的价值。然而,如果人工智能的产出足以媲美甚至超过人们运用其创造力所获得的成果,甚至效率更高、成本更低,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珍视自身的创造力及其价值?
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妨“后退一步”,从种种或激动人心,或贩卖焦虑的叙事与狂想中抽身出来,尝试去了解一些更具基础性的哲学思考。在当下,一个名为“创造力哲学”(Thephilosophyofcreativity)的研究领域正在蓬勃兴起,并跃居到哲学研究的前沿。它综合了心灵哲学,伦理学等领域的资源,力图对我们的困惑予以反思——如何理解人类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究竟具有何种价值,是否值得我们在AI勃兴的年代继续珍视——这些都是“创造力哲学”关注的话题。
撰文|谢廷玉
何为创造力:
新颖与价值、探索与自我揭示
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力”似乎遥远又模糊,常与天才艺术家或重大发明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与它打交道,也常常不自觉地以之为评判标准:看到一幅别出心裁的插画,我们会由衷赞叹“真有创意!”面对一件设计雷同、模仿痕迹过重的“山寨”产品,我们本能地感到审美疲劳甚至反感。
这些感受和评价指向同一个概念——“创造力”。我们似乎天然地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或缺失),却很少停下来思考:在何种情况下,我们会认为一个活动、一个点子或一件作品“有创造力”?这正是许多哲学家反思创造力的起点:“创造力是什么?”
为了理解它,哲学家们提出了多种角度。其中,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Boden)的定义流传甚广。她认为,理解创造力,可以从它产出的成果入手:创造力意味着能“产出新颖的、令人惊奇的和有价值的想法或作品”。此处的关键在于“新颖”和“有价值”。
ElliotPaul&ScottKaufmaneds,ThePhilosophyofCreativity,OxfordUniversityPress,2017
这两个看似浅显的要素实际都值得进一步澄清。就“新颖”而言,博登提醒我们区分两种“新颖”:
(1)历史意义上的新颖: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想法(想想那些重大发明)。
(2)心理意义上的新颖:这种想法对提出者本人来说是全新且令人惊奇的。
不妨想想你自己的生活:你可能曾灵光一现,给同学起了个绝妙的外号,觉得很“有创意”。但这个点子可能早在他/她初高中时就被别人用过了(不具备历史新颖性)。这会影响你起外号时的创造力吗?博登认为不会。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日常生活中的创造力,更多体现为“心理意义上的新颖”——那个外号对你而言是原创的、聪明的点子,这便足够了。
对于“有价值”这个标准又该如何看待?这个标准一度引发争论。想想看:有些想法很有创意,但似乎毫无用处甚至荒诞不经。比如,天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曾研究“读心术”,并构想了一种“思维相机”:
“头脑中形成的图像必然通过反射和折射作用在视网膜上形成相应的图像……只需照亮视网膜,然后拍摄照片,再利用现成的方法将影像投射到屏幕上。如能成功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人脑海中的东西就会在屏幕上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样一来,个人的每个想法都能被读取。那时,我们的思想就像一本本打开的书。”
这是一个看起来颇为新奇,也体现出了创造力的想法。但它似乎没有价值,在技术上也不可行。这样看来,有创造力的活动不需要包含“有价值”这一标准。
哲学家林赛·布雷纳德(LindsayBrainard)为“有价值”的标准做了辩护。她认为,创造活动至少会产生“认知价值”。想想你解一道数学难题:即使最后答案错了,但你在尝试过程中运用了逻辑、进行了推理,这本身就有价值——就像老师给的“过程分”。特斯拉的“思维相机”构想也是如此。虽然想法本身荒谬,但他在构思过程中展现并锻炼了大胆联想、严密推演的能力,这就是一种认知上的收获和训练。
博登的界定借用创造性活动的成果来理解创造力本身。然而,这种界定还不够充分——它至多可以充当“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最多能说,创造性活动一定要产出新颖且有价值的成果,而不能说只要产出了新颖且有价值的产物,某一活动就具有创造力。试想,一株植物也可以孕育出一朵独一无二的花,且这朵花无疑具有价值。然而,我们不会认为植物的孕育具有“创造力”。
这将我们引向更深层的问题:除了成果,创造活动“本身”有什么特质?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观察创造者是如何行动的。
哲学家布雷纳德提出了一个关键类比:创造性活动很像“探索”。它们在两方面高度相似:
首先,二者都朝向未知,目的在过程中浮现。回想你自己动手“做点儿什么”的经历:画画、写东西,甚至策划一次聚会。开始时你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或感觉,不完全清楚最终会做成什么样。创造力往往就发生在这个“模糊变清晰”的过程中:随着你动手尝试(拿起画笔、写下第一句、列出计划),灵感会涌现,想法会改变,最终结果可能连你自己都不曾预料。正如毕加索所说:
“想法仅仅是起点。我很少将它们刚出现在脑海中的样子原原本本地画下来。一旦开始动笔,新的想法就会涌现。要知道自己要画什么,就得先动笔。”
其次,二者都需要高度的敏感性。探索者和创造者都需要极其敏锐的感知力:既要“向内”觉察自己的情绪、思绪、身体感受;也要“向外”捕捉环境中的细节、他人的反应、生活的微妙之处。再以艺术创作为例:“新想法”不会从天而降。它们往往源于创作者从自身经历、观察世界中提炼的灵感,以及对可用工具、技法的灵活调用。
《敏感与自我》
译者:许一诺包向飞
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4月
除了探索,创造活动还有另一个核心特质:“自我揭示”。与植物孕育花朵不同,人类的创造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者不仅仅是在探索一个外在目标,更是在投射和表达内在的“自我”。
想想你真诚地创作或表达的时刻:无论是写一首诗、设计一个方案,还是向朋友讲述一个触动你的故事,其中都融入了你的视角、你的情感、你的理解。你在创造的同时,也在向世界(或特定对象)揭示一部分“你是谁”“你如何看待事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精准地捕捉了这种特质:
“故事不过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这是我内心的感受,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也有同样的感受吗?”
简言之,当我们谈论“创造力”时,我们不仅要想到那些新奇且有价值的成果,更要考量一种独特的“活动方式”:有创造力的实践活动像一场充满未知的探索之旅,要求我们保持敏锐的感知,并在活动过程中揭示和表达着我们自身。
为什么说创造力能够
推动社会联结?
论及创造力的价值,毋庸多言的一点是,人类创造力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产物。但在当下,这类价值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人工智能提供——人们日渐难以分辨某一作品到底出自AI还是人类之手。因此,如果人类创造力还具备某些独有的、难以被取代的价值,那么它不太可能来自“成果”,而是源自创造性活动本身的特质。
一种人类创造力的独有价值正是源于创造性活动“自我揭示”的特质,这种价值便是“社会联结”。在此,仍是前文中提及的美国哲学家林赛·布雷纳德对此做出了详述。
回想一下“自我揭示”意味着什么:因为创造活动往往突破常规,带着自发性,故而创作者的真实关切、情感、思想乃至个人风格,会自然而然地“流淌”进作品里。“社会联结”的价值正是由此而来。
如果你是创作者,那么当你的作品被他人看到、理解、欣赏,你自然会感受到一种深层的认可和联结。就像美国诗人兼公共卫生学者杰里米·诺贝尔所说:
“倘若你的创作成果与他人分享,得到他人的关注、思考和欣赏、你会感到自己被看见、被认可、被见证、被陪伴。通过这种对自我的真实展现,你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
想想你分享过的手工、文字、音乐或哪怕是一个真诚的想法:当获得认可和理解时,那种“被懂得”的感觉,正是创造力带来的珍贵回报。
如果你是欣赏者,那么当你看到一件饱含“自我揭示”的作品,发现其中表达的情感、困惑或洞见,竟与自己内心的感受如此相似,甚至被更精妙地表达出来时,也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和“联结”感。这种“原来不只我这样想/这样感觉”的体验,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抚慰和支持感,拉近我们与他人的距离。
那么,AI创作能带来同样的“社会联结”吗?布雷纳德用自己的经历做了实验:她让AI基于自己的萨摩耶宠物狗生成一幅画作,指令是:“一只睡着的萨摩耶犬,它同时是一朵蓬松的云,飘浮在蓝色的天空中,采用印象派艺术风格。”
布雷纳德使用AI工具生成的萨摩耶图片。
她的指令当然包含了一点儿个人喜好(她的萨摩耶),算是微弱的“自我揭示”。但问题在于,指令之后的所有工作都由AI完成。如此一来,对身为创作者的布雷纳德来说:即使作品获得赞美,她也很难从中获得强烈的“被认可”和“联结”感——因为她清楚,功劳主要属于AI。对观众来说,一旦知道这是AI作品,那种“与作者心灵相通”的共鸣感也极易消散。因为观众会意识到,作品背后并不存在那样一个人——她调动了关于爱犬的所有温暖记忆和观察,倾注了心血和情感去创作,那个输入指令的人也并没有真正做多少深度的“自我揭示”。
正如布雷纳德所说:“最终,这幅图像的观看者对我有关萨摩耶犬的想法,以及我对它们的观察和兴趣知之甚少。”她总结道:
“当我外包创意工作时,我正在模糊自己的个性获得的呈现。我设置了一道屏障,让他人难以察觉我的审美品位与个性的其他方面。”
由此,“社会联结”作为一种人类创造力所独有的价值便得到了确证。布雷纳德格外强调,重视这种价值并不意味着拒绝AI。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有些人并非像她那样简单地下个指令就完事。比如《空间歌剧院》的作者杰森·艾伦,他花了80多个小时与AI反复互动、调试,并用Photoshop软件精心修改。这时,AI更像是一支高级的“画笔”,帮助作者进行更丰富而非贫瘠的“自我揭示”。
AI参与创作的获奖绘画作品《空间歌剧院》。
然而,布雷纳德也表达了一种担忧:AI生成“创意”成果的极端便利性,可能会像“短视频影响深度阅读的习惯”一样,侵蚀人类进行创造的动力。想想短视频:它只是提供了一种信息获取方式,并未直接禁止阅读。甚至有人能有效利用它。但不可否认,它让许多人沉迷于碎片化信息,丧失了长时间专注和深入思考的能力。同样地,AI生成的创意成果唾手可得,它可能让许多人不再愿意“忍受”那个充满未知、需要高度敏感、并在其中不断“自我揭示”的、漫长而曲折的创造过程。
创造力的“探索性”
与自我实现的成长之旅
我们已洞悉创造性活动的“自我揭示”特质如何织就社会联结的纽带。现在,让我们看看创造力的另一个核心特质——“探索性”——如何赋予人类创造力独特且难以替代的价值。
“探索”意味着什么?它总是朝向未知,并常常带来惊奇的体验。但不同的创造活动,其“未知”的程度和“惊奇”的强度大不相同。如玛格丽特·博登区分了三类创造力:
(1)组合式创造力:就像用已知的乐高积木搭出新造型。创造者把熟悉的东西重新排列组合,产生新颖的效果。想想早期电影:最初的“影片”常常就是把几段现成的短片拼接起来。如果某个放映员灵机一动,用不同的顺序拼接这些短片,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就是组合式创造力在闪光。
(2)探索式创造力:它指的是在某一已有的领域之内,部分地按已有的规范进行创造。仍以电影为例,如若某一影片在某一流派之内做出了创新,那么此处出现的就是一种探索式创造力。
(3)“转型式创造力”:带有这种创造力的活动具有颠覆性和开创性:它不满足于现有规则,而是打破旧框架,建立全新的标准,其成果本身就成为未来创作的“灯塔”和范本——就像一部开创了全新艺术风格的电影。
《马男波杰克》剧照。
学者克里斯托弗·巴特尔指出了这种创造力的价值所在:
“原创作品是首次清晰展现某种理念的作品,其理念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为未来的作品提供了新的方向……这种理念的潜能丰富到足以激励后来者采用之。”
那么,AI能实现这种具有“原发性”的转型式创造力,进而达成相关的价值吗?林赛·布雷纳德引用了科幻作家特德·姜的一个例子,来对此加以质疑:
“ChatGPT通过识别训练数据(主要是互联网上的内容)中单词出现顺序的统计规律,并存储这些规律的信息而非全部训练数据,从而对信息进行压缩,姜写道:‘可以把ChatGPT想象成网络上所有文本的一个模糊的JPEG图像。它保留了网络上的大量信息,就像JPEG图像保留了高分辨率图像的大量信息一样。’虽然ChatGPT所做的事情并非完全等同于复制其训练数据,但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其输出注定缺乏原创性,因为它完全是基于他人创作作品的压缩版本进行运作的。”
简言之,AI的创作根基是“压缩”和“统计”海量已有数据。目前,即便是像《空间歌剧院》这样惊艳的AI作品,也还没有展现出那种能颠覆规则、开创全新范式的“转型式”力量。国内学者也指出:
“大语言模型可以说是产生组合式和探索式创造力的绝佳系统。但目前的大语言模型并未涉及打破或改变规则的行为能力,其输出结果只是一种根据提示词来产生的概率分布,所以并不具备转型式创造力。”
科幻纪录片《我们需要谈谈》(AIWeNeedToTalkAboutA.I.,2020)画面。
当然,未来AI能否突破这个瓶颈仍是未知数。所以,“转型式创造力”的价值至少在当下,仍由人类独享。
然而,“探索”特质带来的价值还不止于此。或许你还记得创造性活动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敏感——既要向内觉察自我,也要向外洞察世界。正是在这种全身心投入的探索过程中,作为创造者的你常会经历深刻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
譬如说,你也许原本不知道自己如此着迷于某种色彩搭配——直到你动手调配颜料;你也许在写作时发现自己特别擅长用文字捕捉某种微妙情绪;你会在尝试中找到自己真正热爱和擅长的事物,解锁实现心中目标的新方法和新视角。
这种在探索性的创造中认识自己、塑造自己的旅程是创造性活动带给我们的宝贵价值。而这一点恰是无论多么先进的AI都无法代劳的。它能产出结果,却无法替我们经历那个充满敏感、困惑、顿悟和成长的探索过程,无法实现那份独属于我们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
简言之,面对“创造力焦虑”,关键在于认清人类创造力的独特价值。它远不止于产出“新颖且有价值”的成果,更在于创造过程本身蕴含的“自我揭示”与“探索”特质。“自我揭示”将创作者的情感与思想融入作品,成为与他人深度联结的桥梁;而“探索”的过程,需要我们敏锐感知自我与世界,这本身就是宝贵的“自我发现”与“成长”之旅,并可能孕育颠覆性的创新。
在AI勃兴的年代,珍视创造力不仅是为了成果,更为这联结他人、探索自我的独特生命体验与内在价值。
参考资料:
[1]LindsayBrainar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ThreatofCreativeObsolescence,”Ergo(forthcoming).
[2]LindsayBrainard,“WhatisCreativity?”ThePhilosophicalQuarterly(forthcoming).
[3]LindsayBrainard,“TheCuriousCaseofUncuriousCreation,”Inquiry68(4):1133-1163(2025).
[4]LindsayBrainard,“ArtificialIntelligence,Creativity,andThePrecarityofHumanConnection,”OxfordIntersections:AIinSociety(2025).
[5]简小烜,束海波:《大语言模型创造力的哲学探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4月28日。
作者/谢廷玉
编辑/李永博
校对/赵琳